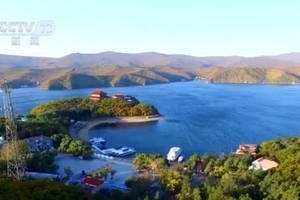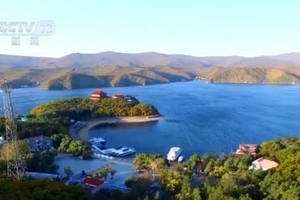|
糖尿病病因 http://www.national-tnb.com/by/ 前两天,大米和小米收到了一位美国妈妈的来信。 通过来信内容,可以看出,她应该是最拼命的那一类母亲,身怀二胎也在争分夺秒给孩子干预,自学康复,攻读BCBA课程,要生产的头一天还在给老大做康复活动。 但她每天要面对的,却是一个在密集干预下,能力依然持续倒退的重度自闭症孩子: 这个孩子原本8个月时就会叫爸爸妈妈,1岁半会识字,抱出去备受欢迎,从两岁起,却开始“断崖式倒退”。 他越来越难带,会说的词汇越来越少,到了4岁时,除了疼叫“哇哇”(上海话),其他词一个也不会了。 如果生活不断下坠,往哪个方向努力,都是黑暗,这条路又该如何走下去?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妈妈,倾听一个重度自闭症家庭发出的声音! 80后上海人。 赴美读研,从东部费城搬到中部芝加哥,最后到西部湾区硅谷安家,育有1个重度自闭症哥哥,和一个活泼可爱的妹妹。 因为孩子,改道学习行为分析学,现为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在读认证行为分析师(BCBA)。辅助儿子的同时,也盼望能陪伴和帮助其他自闭症孩子和他们的家庭。 1 养育一个重度自闭症孩子 兵荒马乱是日常 电话铃响起,我一看是社工的电话,赶紧接了起来。“喂,我是,现在可以。” 我一边回答,一边盯着因我接电话而从课桌边逃走的儿子。 “真的啊?可以批下来?那太好了。谢谢你!”得知我申请了四个月的政府补贴休息时间终于批下来了,我有些激动。 “你等一下,我拿笔记一下。” 突然,嗅觉敏锐的我闻到了一股臭味。抬头,两坨大便在客厅地毯上是如此醒目,儿子的手还在摸屁股。 “对不起,我实在不能再说了。我先填起来,有什么不懂的我再问你。谢谢!” 我把电话扔在一边,冲过去,拉住儿子的手,开始了新一轮的处理…… 我儿子5岁8个月,是一个重度自闭症患儿,这样兵荒马乱的场景,是我每天的日常, 2 “我是你妈妈” 生我儿子时,是剖腹产。 因为美国医院的死板,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波折,才终于迎来了他的哭声。 术后5小时,当病房里只有我一个大人时,我第一次抱起我的儿子,他看着我,我看着他。 他的眼睛好黑,整个眼眶里都是黑色,反射着灯光,就觉着特别亮。他看着我的样子,好像是在审视我,问我“你是谁?”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连结。 不是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,而是那个对视,把我们连在了一起。“我是你妈妈。”我回答他。 之后,便是新手妈妈大多都会经历的痛苦:喂奶的疼,睡不好的苦。 “会好起来的。”我妈这么跟我说。 因为自己长得矮,而与心爱的演员职业无缘,我心里最在意的是儿子的身高。 男孩子,更不可以长得矮。 我细心地喂食,用心地陪他玩。努力没有让我失望,一岁半前,他的身高、体重都“名列前茅”,8个月就会叫爸爸妈妈,一岁半会识字,抱出去时大家都觉得他可爱极了。 虽然他的睡觉一直是个问题,晚上总是频繁醒来,但其他方面都发育良好,我也想着,也许真的会好起来。 但一切,却在不知不觉间变了。 3 32岁生日 我拿到了儿子的自闭症诊断 儿子22个月的时候,说话比以前少了,脾气坏了很多。 那时,我以为这就是所谓的terribletwo(糟糕的2岁)提前到了,不是他不会说,而是他不想说。 24个月的时候,他的词汇量继续倒退,动不动就哭闹,让他做什么都不配合,对食物又格外挑剔,加上睡觉一直不好,他俨然成了一个很难带的孩子了。 “别人带几个孩子还可以上班,为什么你带一个孩子还这么多抱怨?”丈夫问我。 很快我们找到了原因。 4月是自闭症科普月,随着铺天盖地和自闭症相关的信息一条条地和儿子对上号,我们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。 这个共同的危机让我和丈夫暂时放下了我们之间的矛盾,同心合力地去找解决方案。 去斯坦福诊断要排队6个月,去医疗保险挂钩的医院要等7个月,可孩子等不起,我们立刻掏出6000美金私费去做诊断。 诊断持续了3天,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专业人员把很多玩具放在地上,然后看孩子会怎么玩。结果我儿子踮着脚,嘴里念着火星语,在这些玩具中打着转,踩到了也毫无所谓。我丈夫当场就崩溃了。 32岁生日前两天,我拿到了儿子的诊断报告:自闭症,中重度。 虽然这个结果已经是预料中的了,诊断只是一个必需的过程,需要诊断报告才可以给他安排干预,但是当时的我还是低估了那几个字的分量。 4 无法抵抗的倒退 而立之年,我的人生轨迹变了。 我和我丈夫很不同。 他收到诊断书后,开始哭,天天哭,见人就哭。但我都不记得自己掉过眼泪,甚至连经典的“为什么是我?”都没有问。 行动派的我打印出了近百条干预机构的信息,一边带着孩子,一边一家家的打电话安排立刻干预。 我们所在的加州湾区/硅谷有三高:工资高、房价高、自闭症儿童比例高。在湾区,有干预资质的康复师和自闭症儿童的数量不成比例,供不应求的市场使得排队成了必然。 但是孩子等不起。我一边自学干预,和孩子在家里操练,一边趁他午睡时给机构打电话、催着他们,就为了逮住一个可能的空隙。 终于,不知是我的软磨硬泡把园长烦得不行,还是我的认真执着打动了她,我的孩子得到了一个位置,而且这个机构自带融合幼儿园,在湾区华人中有不小的名气! 剖宫生女儿的前10天,我儿子第一次进了机构幼儿园开始了系统的干预。 但即使有专业人士给儿子干预,我也从来没有松懈过。 生女儿的前一天,我陪着儿子和来家里辅导他的老师一起做游戏、进行教学。生了女儿后的两小时,我躺在病床上看着手机里传来的家里的监控录像,记录着老师给儿子上课的情形。 ......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从我儿子26个月时怀疑他有自闭症,到他4岁的那段时间,我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。 每天只刷一次牙了,能洗个澡成了莫大的奢侈。我都不知道朋友圈是何物。天下大事,与我何干?那些日子,我体会到了没有最累,只有更累。 那个时候,幼儿园干预机构的园长和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不要放弃。”“我当然不会放弃,这还用你说?”我心里想着,一直没有过多思考她这句话的意思。 然而,即使这样努力的付出,我还是阻挡不了儿子的倒退。 四岁生日前几天,他的词汇量正式降为了1,除了疼的时候,他会说“哇哇”(上海话),其他的词一个也不会了。不会叫爸爸妈妈,Hi,Bye,要吃的东西,什么都不会说了。 5 从零开始,重新找回的语言 面对丈夫的打击,孩子的持续倒退,我依然没有放弃。 我记得和儿子的那个对视,记得自己对他的回答:“我是你妈妈。” 他四岁时候,我带他参加了斯坦福的核心反应训练(PRT)教导语言的实验项目。 当时我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去的:词汇都已经倒退到1了,还能更差吗? 总的来说,PRT的精髓就是找孩子感兴趣的东西,然后一旦他说出来,或者接近说出来,就把这个东西给他。 用在我儿子身上,就是,他特别喜欢吃冻干草莓。我举着冻干草莓,说“莓莓”,他只要一模仿说“莓莓”,或者哪怕只是发了一个“M”的音,我就立刻把冻干草莓给他。 就一个“莓莓”,我们练了整整三周。就当老师也感到手足无措时,我儿子居然终于明白了这是要他干什么。他说了“莓莓”,我赶紧给他,他吃得开心。我再举着一小块,说“莓莓”,他说“莓莓”,我再给他。然后我开始慢慢消退对他的提示,我举着冻干草莓,但是不说话,等他一说出来“莓莓”,就立刻给他。 我们从一个词“莓莓”,拓展到“可可”(巧克力),到“On”(看视频);再从单音节词到多音节词…… 我儿子总算开始说话了! 多音节的词一开始是很困难的,他的口部肌肉弱,要把不同的发音组合在一起时就乱了。我会举两张牌子提示他有两个音,一个个分开念,练习久了再衔接得快一点,等熟练了再慢慢撤掉这样的辅助。 从4岁到4岁半,我儿子终于慢慢学会了一些单词,基本上都是生活中他爱吃的东西,或者和看视频相关的词汇。然后学会了一些基本命名,再是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,比如姓名、年龄等。 6 患上抑郁症 我终究只是个平凡人 可就在儿子慢慢多说几个单词的同时,我出了状况。 几乎是毫无预兆的,我感觉自己得了抑郁症。 对于孩子终于开始的进步,我高兴不起来,整个人都陷在一种低沉的情绪中。 于是,我选择把聪明活泼、确定没有自闭症的女儿送到了幼儿园,虽然她还没有到两岁,但考虑到我当时的状态,我判断她去幼儿园会比待在我身边好。 终于有了一点静下来的时间。在思考中,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自己“突然”陷入忧郁了。 因为我的孩子就快5岁了,那个干预的黄金期就快要过了,而回顾过去将近3年的干预,我认为我的付出和收获是不成比例的。 为了他“可能”的进步,我付上了不计其数的代价,而之后的失望给我的打击则比拿到诊断书时更为沉重。 我也没有后悔自己的付出,但我确实是累了。有人问我,为什么可以如此没有自我地付出那么久,我的回答是两个字:责任。 可我突然发现,我终究是人,一个很平凡的人。 这些年我很少看他人写的文章,但有一次在自闭症专栏中我读到一篇住在加拿大的上海人写的文章,说她为了自闭症孩子,父母过世时都没有回上海,等可以回去时,家里只有父母的遗像了。 看完那篇文章,我哭到停不下来。我也爱我的父母,想在他们身边尽孝。 可我已经几年没有回父母家了,因为我孩子的干预不能断。我只能给我妈买保健品、买衣服,把她的行李箱塞得满满的,然后送她去机场。 这些年,我不是女儿,不是妻子,不是哪个公司的雇员,不是某某兴趣爱好者,甚至不是一个人,只是一个重度自闭症孩子的母亲。这单一而又沉重的身份,终究是把我压垮了。 7 写小说,考BCBA 找回重度自闭症患儿母亲外的我自己 送老二去幼儿园后,我开始去机构工作,成了一位干预自闭症的康复师。 本科985、留美两个硕士学位的我学习能力还挺强的,再加上这些年学干预孩子的经验,已经使我不亚于一位科班出身的特教康复师。 而在机构工作后,我明白了,康复师的身份和母亲的身份终究是不一样的。 康复师可以下班,妈妈不可以; 作为康复师,当我对着一个孩子,我会全心全意地辅导他,我整个人的状态是很轻松的,没有什么压力; 我也可以跳脱出来,以第三方的角度去看问题; 总之,这份工作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转机,是我对抗抑郁情绪的开始。 我意识到,我需要从一个重度自闭症患儿母亲的身份中抽离出来些许,做好我自己,这样才能在与自闭症奋斗的这场马拉松中更好、更持久地照顾、帮助我的孩子。 孩子四岁半后,我每天会特意给自己安排一个多小时的时间,犒劳自己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我开始写小说/剧本,以另一种形式去实现曾经的演员梦。 在我的小说中,女主角还是要与自闭症奋斗,但她的努力从长远来看是很有效果的,而她本人也在各种挑战中不断成长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而通过写作,我的内心得到了治愈,我有了更多的心力去面对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。 2020年初,我还开始正式选修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BCBA(BoardCertifiedBehaviorAnalyst认证行为分析师)的课程,并在干预机构中继续工作。 现在,我依然是一个重度自闭症孩子的母亲,我依然每天忙碌于孩子的干预和生活,目前的我说不出“你是我最好的礼物”这句在自闭症题材电影中常出现的话。 但有一点,我依然坚守着:不要放弃,哪怕每天能做的很少很少,也不要放弃: 在行动上不放弃用科学的方法,帮助孩子提高交流和学习的能力;在心态上不放弃对未来的希望。 他依然会进步,虽然进步的速度很慢很慢,虽然比同龄人落后很多很多,但他同样有自己的道路。 同时,我也要渐渐成为我自己,和他一起成长。 也许有一天,我的孩子会明白,我一直记得和他的对视。 “我是你妈妈。”这是我对你今生的承诺。 手拉手的母子三人 -END- 编辑|小熊当当主编|潘采夫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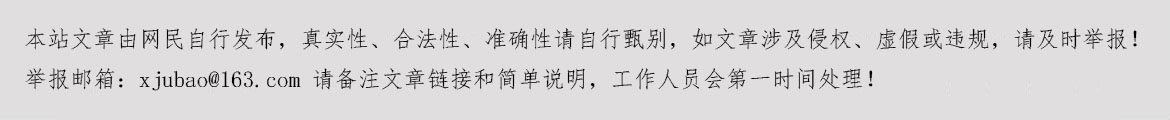
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• 新闻资讯
• 活动频道
更多
更多